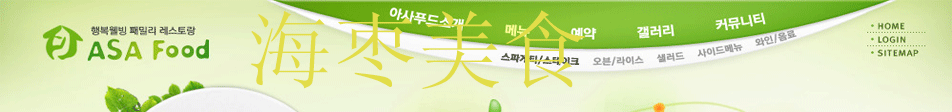|
初到喀什 年9月,我踏上了去喀什的路途。 地处南疆、连接欧亚的喀什被誉为中国最具“异域风情”的城市,这里货如云屯、人如蜂聚。穿行在老城的民居小巷,浓郁的西域文化和淳朴的民俗让人仿佛置身于时空隧道,但是,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也使得拍摄过程时常伴随着尴尬与质疑……清冷的新月和炙热的土地交织在一起,喀什,应该是一个能在年老之时给我带来无限回忆的地方。 在去喀什之前,我所做的唯一的功课就是看了一下穆斯林的若干禁忌,以防在喀什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除此之外,我没有“预习”有关当地的任何“知识”。我要的就是把自己对一个地方的感受保持在最彻底的白纸状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色彩。 但是一俟踏上这个中国最西陲的城市,才发现这里异国情调相当的浓厚。如果不是学校大楼顶上的国旗和操场上的孩子们用汉语唱的《歌唱祖国》提醒我这是在中国,恍惚里还真会觉得已经置身于喀布尔或者伊斯兰堡的某个街口。混迹于当地人中,蒙古鞑靼人种特有的特征表明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国人”,喀什老城里的孩子们看到我张口就来“哈啰”,打闹着争夺我带去的糖果,使我越发觉得在这里我和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游客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大一点的青年人则会拘谨得多,琥珀色的瞳仁里透出毫不掩饰的对外来者的警惕,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奇心。伊斯兰教严格的教义在他们身上已然显现,开始规范他们的言行举止。 我到达的9月中旬正好是穆斯林的斋月期间。直到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在旅馆附近的若干家穆斯林餐馆连续吃了几次闭门羹——维族餐厅在封斋期间白天几乎是不营业的,而在老城里是几乎不可能找到汉族餐厅的。最后我不得不在某餐饮互联网点评榜上有名的“银提尕尔”旅游餐厅了却每天的早午饭。 按照《古兰经》的教义,除了孕妇或者哺乳期的妇女、病人、婴幼儿,正在作战的士兵以及在日出前踏上旅途的人之外,全体穆斯林都应该参加斋月接受斋戒——即每天在太阳升起之前摸黑起床吃“封斋饭”,一直到晚上9点天全黑才开始吃第二顿,整个白天不吃不喝,禁绝烟酒、房事。斋月结束后的第二天就是伊斯兰教两大著名节日之一的开斋节,又叫“肉孜节”。节日的早上穆斯林们去清真寺做会礼,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由于假期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待到开斋节狂欢的这一天。满街跪祷的壮观场面固然更具视觉冲击力,但是我更喜欢那种浸透在日常中的宗教细节,不动声色却又充满力量。的确,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信仰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高于生活。掀开神秘的宗教面纱,平淡的日常中信仰就是奔头。每天当太阳完全沉没于地平线之下,喀什老街的不少主要街口都设有桌子摆满西瓜、哈密瓜和馕等食物供封斋一天的维民免费食用。每每看到人们围桌狼吞的场景,我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突然感到了信仰的力量原来就是如此的真切。 位于喀什老城内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寺之一,也是喀什市绝对的地标。大门前的台阶上永远有三三两两的维吾尔族老人坐着闲聊。进得大门,门楼的两旁不对称地各竖有一个18米高的宣礼塔。每日黎明,寺中阿匐要五次登上塔高声呼唤穆斯林们前来礼拜。拜访清真寺的那天下午,头裹纱丽的维族女讲解员带领我们穿越过清真寺的厅堂殿室,用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向我们介绍清真寺的历史和穆斯林的习俗。她特意向我们强调,女子只能在家中进行祷告,不能在街上祷告更不允许进入清真寺。我们下意识地问道:“那你怎么在清真寺里呢?”女讲解员愣了下马上严肃回答:“因为我是导游。”神色庄严到完全不认为这是一个半带着玩笑的问题。随后她快步带着我们经过了一群正在祷告的穆斯林身边,教徒们正在阿訇的带领下做每天的五次祷告之一的晌礼,即完成“五功”之一的“拜功”。 长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