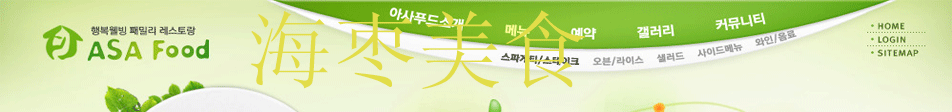|
治疗白癜风的外用药 http://m.39.net/nk/a_4639949.html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被派往新疆喀什地区支援工作,九十年代初,才调回南京。在喀什工作的十七年里,经历的艰苦生活和艰苦程度,生活在内地的人们很难遇见,没有相关经历的人,也很难想象和理解。 防疫工作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常年在基层,在田野,在维族老乡中,整天泥身灰面,在当地维族老乡中,流传着“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原来是个搞防疫的”的笑话。如今老了,反过来想,正因为我们曾经历过那么多艰苦生活,那么多艰难工作环境的磨炼,使意志得到磨练,身心得到锻炼,同时也夯实业务基础,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为以后在人生之路上,遇到各类难关,面对各类艰难,提供了珍贵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记得那是一九六五年八月的一天,我正在莎车县十一公社的实验室里紧张操作,突听门外有人在大声叫:“孙本渝,指挥部来电话了,要你与刘国强马上赶到麦盖提县去”。十一公社,是一个边远的公社,离县城有五六十公里。 长期的防疫工作,让我养成了行动迅速的军人作风。我很快就准备妥当了上路的一切。当时,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维族老乡特有的行囊——“马搭子”,它是一种以粗棉线编织而成的、原用于骡马背驮的装载用具,被褥、衣服、用具、书籍等等,全都可以装进去,扎好了袢扣,便可肩扛着行走,搭乘马车、卡车时,可当坐垫;马搭子编织得很密,外面看着蒙着灰尘,里面的东西却干干净净。行装准备完毕,公社派大马车,送我和刘国强去麦盖提县。 抄近路去麦盖提县,必须要渡过叶尔羌河。 下了马车一看,哇!它比长江在南京地域的江面还宽。之前就知道,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大的支流,具有内陆河典型特性,没有固定河床,现在水在这一处流,过段时间,水又会突然跑到另一处流,长此以往,河面也就十分宽阔;内陆河的另一个特征是,夏季丰水期,水量极大,流速也极快,因多为雪山冰雪融化,水温也很低。横渡叶尔羌河,一会儿需要淌水,一会儿又需坐船,过一次河,中间要反反复复多次。 下了马车,我俩扛着各自的“马搭子”,随着人群,淌着水,来到一艘木船边,买票登船。这艘木船是一种平底船,河面上空,有一条钢索横跨两岸,船上又有钢绳套在钢索上,利用水流,滑行着前进,就这样前进了没多久,水又变浅了,船触底搁浅了,船员跳下水,喊叫着要乘客下水,一起淌水推船,多数乘客看着船下依然湍急的水流,都迟疑着不敢下水,急得冒火的船员,站在船帮边儿上,把男男女女的乘客,一个个地往船下拽。不知为什么,船夫把大家都赶到了水里去推船,却唯独放过了我们,也许,是我们的“刀合特尔(维吾尔语:医生。编者注)”身份吧。数次折腾后,木船终于了抵达对岸,医院的救护车,已在河对岸迎候。 又有一年的初春,为落实周总理关于开展“老年性慢性气管炎”的调研工作的指示,我与几位同事,被派往泽普县开展相关调研工作。工作点,选在离县城三四十公里的“依革苏”公社。当时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基层生活环境极其简陋,医院出发前,需要备好工作人员一周所需的主食白面馕,装着一并带走。“依革苏”这个地名,按维吾尔语释义,是“两条河”或“两处水”,但我们到达工作点时,连一滴水都找不到。维吾尔族老乡,是在已经干涸的水渠底部,向下挖一个水井样的深坑,然后用胡芦做的水舀子,把坑底渗出的水,一舀一舀地舀上来,半天才可舀一小铁桶水,这,就是我们工作队一行数人,整整一天的饮食用水。 至于洗漱,那就别想了,无论早晨起床,还是一天外出工作归来,都没一滴水可供洗漱,而且还是一连六天,天天如此,只有等到星期天,利用返回县城休整的机会,才有可能彻底洗漱一遍。好在,新疆气候干燥,一周不洗漱,也没有什么不适,要是在内地,尤其是南方,一周不洗,那全身都馊了,臭了。 当时南疆乡下,因多种因素影响,维族老乡饮食单一,主食玉米,少许牛羊肉类,蔬菜水果极少,冬春之交尤甚。因绿色植物摄入过少,引发的患维生素缺乏症、癞皮病等多发病、地方病比比皆是。当地卫生防疫单位虽然每年春季向村民们发放VitPP(烟胺酸),预防和控制此病,但因交通,信息等影响,效果可想而知。 工作点没有蔬菜可买,决定了我们一成不变的食谱:早餐,玉米糊糊;午餐,馕;晚餐,“苏嘎西(维吾尔语:汤面。编者注)”,维族老乡采集未熟的杏子,“恰马古(新疆一种块茎蔬菜的维吾尔语称谓。编者注)”,面片,煮成一锅。 馕(维吾尔族主食,一种以小麦或玉米粉加水揉制、烤制的干粮。编者注),一般是可以长期存放的,但那主要是指片馕,医院给我们供应是团馕,这种馕放置几天后掰开,也可见到有长长的霉丝,闻到异味,但除了强忍着下咽,别无他法,不然就得饿肚子。再说,即使如此,我们工作点的伙食,比之维族老乡那日复一日硬如岩石的包谷馕,已是天堂级别。 周日返县城时,是没有公共交通工具的,只能搭便车,即搭乘路过的免费卡车,在灰尘满天的公路边,所有经过的汽车均未理会我们的拦阻,一路绝尘而去。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利用男人好色的弱点,请队里的女同志出面拦车,男同志隐藏在路边,一旦司机停车与拦车女同志搭话,男同志便立即蹿出,迅速爬上车厢。司机发现情况正想开骂,搭车女同志告诉他,我们都是一起的,把司机鼻子气得歪歪,但又无可奈何,只得一起带着走,下车时,我们这群打劫者,还虚情假意地向司机道谢不已。 一次,叶城县畜牧场发生疫情,领导派我与春夏娃子(作者的一位维吾尔族同事。编者注)一同前往了解情况、做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因要去的地方邻近西藏,当时只有军车才去那个方向。我们到叶城县后,随即赶往南疆军区驻叶城兵站,搭乘去西藏的军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军车的货物上,用自己的“马搭子”作坐垫,一路颠簸,尘土铺天盖地,最后终于到达柯克牙(新疆地名。编者注)公社。柯克牙,不但是叶城县、也是全新疆最南端的行政单位,翻过距此不远的“冰大坂”,便进入西藏阿里地区。 柯克牙,地处喀喇昆仑山山麓,几座简单平房,一片寂静荒凉,四下了无人烟,连一棵树都没有。费很大劲,才找到了当地老乡,至于是租用了毛驴车还是牦牛,现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是穿越了一大片戈壁滩,暮色四合时分,又饥又饿的我们,才抵达县畜牧场场部。 场部空空荡荡,不见一人,好容易找到一个,好像还有点精神毛病,把我们带到一间破旧空房间前,扭头便走,再也不见回来。这里已是高寒地带,房子门窗破旧,四处漏风,我们只得四处寻找树枝、木棍,生起火来,紧裹着皮大衣,坐在行李上,熬到天亮,迅速忙完工作,快速撤离这难忘的地方。 一次,与马木提汗(作者的另一位维吾尔同事。编者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四周被沙漠包围的麦盖提县四公社,开展疫苗注射工作。为提高接种率,还需要穿越沙漠、到一个偏僻生产大队开展注射。这是我在新疆十八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穿越大沙漠。记得当时请了当地一位老乡作向导,大家骑着骆驼,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丘一个连着一个,四周看起来无任何差异,也没有任何特殊标记,事后,我敬佩那位向导带路本事之余,也曾有些后怕,万一,他带偏了路,走进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等待我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有年春季,我们去兵团农三师所属五十一、五十二团开展“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病学调研工作。这些团场在巴楚县靠近阿克苏地区一侧,距离巴楚县城很远,正值道路“翻浆”时期。 “翻浆”,是新疆地区的公路因春季地温上升、冻土融化,加之过车应力,使路面或沉陷或抬升并布满泥泞的现象。我们那次去,路况极坏,汽车被陷在烂泥寸步难行。夜里,团场派一辆“东方红”履带拖拉机,牵拉着汽车,在“翻浆”路上行驶。四野漆黑一片,在昏黄车灯光照射下,路面像沼泽一样,泛着灯光,拖拉机不断加大马力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而坐在汽车里的我们,被颠簸得已到了骨头快散架的地步,人的精神,也被摇晃得进入麻木,行进过程中,有几次汽车几乎倾翻,大伙都不知躲让,折腾到深夜,汽车上的我们,总算被拖到了目的地。 还有一年,突然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股挖掘中草药之风,按照上级指示,我们把喀什周边中草药材收集完后,便再去柯克牙,到喀喇昆仑山麓采集雪莲。路途非常险恶,一边是高山斜坡,另一边是悬崖断壁,路基下深远的底部,传来潺潺流水声,患有恐高症的我,坐在单位派的“跃进牌”卡车上,紧张得不敢东张西望。等车开到能见到雪莲零星开放之处,海拔已较高,高寒兼缺氧,行动困难,数人互助,方完成采集,打道回营。 在喀什地区工作时经历的艰苦工作和生活,虽已成为过去。我想,还是让那些艰难,那些艰苦工作和生活,像时间一样,通通一去不复返吧,不要让我们的后辈,再去吃那份苦,遭那份罪! 题图及文中图片,系推文时编者所加,仅用于表意或活跃版面,与文中内容无直接关联,图片来自网络,如有无意冒犯或侵权,请尽快通知我们删除。 孫本渝,男,一九四三年生,小学,中学,大学均在南京市,工作南京市卫生防疫站,因新疆发生疫情,一九六五年调至新疆喀什地区流行病防治所工作,一九八二年调回南京市卫生防疫站,现已退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 |